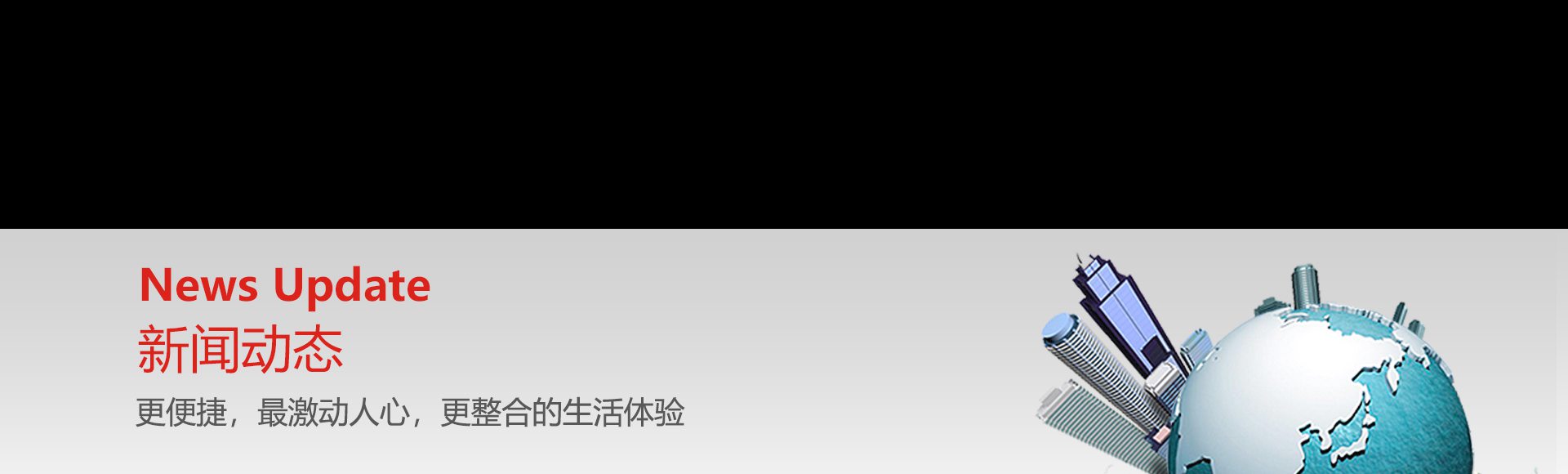敦煌藝術美學巡禮
2020-02-13 15:39:29
admin
傳神是藝術的最高境界
東方的藝術以傳神著稱于世,這在敦煌莫高窟4.5萬平方米的壁畫和2000多身的彩塑中也無處不體現著。“神”主宰了莫高窟藝術的一切。然而,在這些歷時中國近十個朝代的492個洞窟中,莫高窟第158窟涅槃佛,應數得上是莫高窟藝術中的“神”中之神了。158窟的涅槃佛,是9世紀后半葉的作品。“涅槃”用俗話來說就是“死”了,佛教則認為涅槃是人進入不生不滅的境界,是永生的象征。如何表現這一雖死猶生的復雜而又矛盾的場面?我們看,佛涅槃了,五百弟子圍于四周號啕大哭,痛不欲生。有的割鼻、割耳、刺腹來表示對佛陀的哀悼,但我們看到了佛祖釋迦牟尼并沒有死,一張安詳的臉,恬靜而又莊重,富有張力的鼻翼似乎可以聽到有節奏的呼吸聲。右手枕側而臥,這只有活人休息時才會做出的姿態!釋迦確實沒有死,他正進入禪定的夢境,看那半閉似動的眼睛,不正是人在熟睡進入夢境時自然啟開的狀況嗎?不錯,嘴角還露出夢的微笑。“最高的藝術是夢”!這是西方現代派藝術家最后發出的無可奈何的嘆息。然而,中國古代的藝術大師們正是把釋迦牟尼的死處理在夢境之中。如此高超絕妙,簡直是一首美妙無比的夢的贊美詩!這使我們聯想起西方基督教里十字架上的耶穌,赤身裸體,手腳被釘在十字架上,鮮血直流,低垂著腦袋,張開的嘴巴曾呼出過他垂死的一息,松弛的肌肉和拉長的形體足使每一個人相信,這是一具絕對死去的尸體!加上塑造的真實,多么令人恐怖。也許這是西方人喜歡“化悲痛為力量”的審美習慣,但作為東方人看來,會使人感到現實的慘淡和失望。是不是釋迦牟尼死的時候就沒有痛苦呢?不是的,根據佛經的記載,釋迦牟尼已知道自己即將涅槃,于是與諸比丘來到鳩尸那城力士生地娑羅林外,釋迦對阿難說:“汝可往至娑羅林中。見有雙樹。孤在一處灑掃其下,使令清凈,安處繩床,令頭北首。我令身體極苦疲極。”顯然,釋迦死的時候也是很痛苦的。從而我們看出,這是兩種絕然不同的藝術表現手法:東方藝術善于表現“精神”的永在,西方藝術則重于表現現實的永恒。我認為,要談論東西方藝術的表現手法的異同,從這兩個例子作為開始是再好不過了。
運動是藝術的生命
列奧納多•達•芬奇說過:“運動是一切生命的源泉。”(《芬奇論繪畫》第161頁)19世紀法國著名雕塑家羅丹也說過:“畫家或雕塑家要是人物有動作,所做的便是這一類的變形。他所表達的從這一姿態到另一姿態的過程……在他的作品中,還可以識辨出已成為過去的部分,也可以看到將要發生的部分。”(《羅丹藝術論》第73頁)追隨藝術生命的運動,表現宇宙生生不息的運動秩序,在我們偉大的祖先更是優秀卓越的。莫高窟北周時期第290窟中心柱背后的“胡人馴馬”就是表現這種連續運動的例子。我們先不看這位胡人的上半身,而是先從這位胡人馬夫翹起的腳后跟看起,從這雙翹起的腳后跟和兩只向前傾的小腿可以看出,馬夫的身子剛剛向前傾過,并用力甩出過一鞭,而這匹烈馬被迫退縮了。我們從馬的后腿看出,這一鞭確實使他吃驚不小,但馬夫稍一收鞭,烈馬又急蹬起前蹄,踢向馬夫,馬夫也躲閃不急,上身趕緊向后傾斜。這一往一返,一張一弛,多么精彩生動!簡直是一組驚險的電影鏡頭。類似這種連環動作的畫面在莫高窟還有許多,如西魏時期的285窟窟頂東壁北側的兩只飛天鵝,按平常所見,飛鳥的翅膀都應是前后運動的,但畫者為了表現飛鳥的前后連續運動,把每只天鵝的翅膀畫得一前一后,以示運動的過去和現在這兩個時空。羅丹又在分析18世紀法國著名畫家席里柯的《愛普松的賽馬》時說:“他畫的馬,像俗語說的那樣,肚子碰著地奔跑——就是說馬蹄同時伸向前后。……照片中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不錯,在快相中,當馬的前蹄到了前面,后蹄一蹬推動全身,又立刻收回到腹部下面來,預備再蹬——這便使得四腳幾乎懸空的收攏在一起……”“我深信席里柯反對照相是有理由的。因為他的馬確實像在奔跑……既然他是我們所見到的真實,給我們深刻印象的真實,而我們認為重要的,就是這種唯一的真實。” (《羅丹藝術論》第41頁)席里柯表現的這種奔馬的連續運動的畫面,在敦煌壁畫中就更多了,舉不勝舉。如北周時期428窟東壁南側的舍身飼虎圖中的二位兄長飛馬回報父母的場面,還有第156窟的張議潮出行圖、宋國夫人出行圖中的許多奔馬姿勢都是如此表現的。當然,這些畫要比羅丹論述的作品早一千多年,但在中國,遠遠還不止,早在公元前117年的漢代霍去病墓前的石刻藝術中就已運用過這一手法。陜西霍去病墓前有石刻“躍馬”,這座命名為“躍馬”的石刻,馬并沒有躍起,從它的后腿看出,馬的過去是在臥地休息;而馬的前蹄此時內蹬刨地,當人們一看到馬的前蹄做出如此動作時,便知馬即將一躍而起。這個雕刻不僅完善地表現了過去、現在兩個連環動作,而且會立即產生“躍”的第三個動作,巧妙地表現了運動的過去、現在、將來這三個時間空間。
情感在空間的塑造
大自然賦予詩人以詩的感情,巴黎凱旋門前的建筑賦予貝多芬《英雄交響曲》的旋律。同樣,藝術家制造出某種空間,來達到同等的藝術效果,這種空間的塑造多用于建筑藝術。而在中國的石窟藝術中,藝術家們常與畫面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來塑造這種情感的空間。莫高窟西魏時期的249、285窟和唐代的45窟是最好的例子。在北魏時期,由于佛教藝術輸入不久,明顯地受到外來藝術的影響,洞窟窟形也受到印度的影響,多呈中心柱式結構。到西魏時期,窟形改變為天頂式,從窟頂上所畫的中國神話傳說故事來看,這種窟形是受到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響。其中第285窟的窟形大小以及畫面仿佛不存在了,完全融化在空氣里,只有神思在飛揚。四周的壁畫把人引入到一個夢幻的境界,蒼穹天體,空曠明朗,時而天神,時而魔鬼,時而怪獸,時而仙女,回旋飛馳,虛實對比。這些虛實幻覺的雜編正是人的夢覺的再現。由于洞窟窟形的嚴謹,會使這些夢覺緊箍著腦海,久久無法平息。令人奇怪的是,當人離開這些洞窟時,腦海的記憶留下更多的也只是這些夢覺,猶如夢中醒來,剩下夢的記憶。雖然我們經常來到這些洞窟,但似乎總無法記清里面的許多東西,好像這些洞窟里的東西是“無限”。唯有這種夢覺卻久久無法忘懷。夢的世界,夢的藝術,正是西方現代派藝術家們夢寐以求的境界。
一般人的正常視覺,在視圈內看到的物體都會呈近大遠小,在西方繪畫藝術中叫作透視焦點。唐代第45窟,利用了這種焦點透視的視覺常理,完美地表達了畫面與空間的情感塑造。16世紀意大利著名畫家列奧納多•達•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壁畫,他描畫的是基督耶穌在受難之前與十二個門徒共聚最后的晚餐,當耶穌突然說出:“我現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出賣我了。”門徒們驚呆,彼此對看。達•芬奇的畫面就是表現這一瞬間的。為了突出這一戲劇性高潮,作者將全幅畫中的所有景物透視線消失在最中間的耶穌頭上,這一高妙的手法,已在中外畫壇被論為一絕。然而,莫高窟第45窟佛龕上的塑像群排列就是按這種透視而定的。45窟,是公元8世紀我國盛唐時期的作品。全窟佛龕上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天王共七個塑像。以佛為中心依次向兩旁呈放射性排列。當我們走進45窟站在中間觀望時,佛龕上兩邊的塑像高低不等。中間最高,前面的天王最矮,所有塑像的眼睛視線是朝地下看的。當我們以一個佛教徒的身份,在近佛龕中間跪下仰望時,會發現這些高矮不等的塑像,成了一條近大遠小的透視線,前面原來最矮的天王成了最高點,依次向中間的焦點集中,而這兩邊形成的透視線正消失在正中的佛塑像身上。與此同時,還會發現佛龕上所有塑像的眼睛視線一齊正視著你,形成了第二個視線焦點。試想在那香火旺盛的年代,在這個光線微暗的洞子里,燭火閃爍,香煙繚繞,一個佛教徒來此跪拜,仰望佛龕,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中間至高無上的佛,再看兩邊的弟子、菩薩,目光一齊朝你,覷視著你的全部心靈,真善與丑惡在心靈中戰栗,“邪惡必定得到報應”!這是最前面兩邊天王發出的吼聲。緊縮的心靈又重新回到對中間佛陀的祈禱,從佛的“施無畏”右手得到了懺悔,在佛的“與愿心”左手得到了安慰。
整體——藝術塑造手法的根本
上面已述過,藝術塑造的整體是何等的重要,然而,對于每個從事藝術創造的人來說又是何等之難。它貫穿了藝術創造的全部過程,包括了一切表現手法、思想、情感,并賦予作品以生命和神。它似乎是無形的,但它是藝術生命的血液。上述眾多的例子,都足以說明中國古代的藝術大師們對塑造整體的卓越天才。這里再重述幾個例子來闡明這個問題的重要。莫高窟第259窟西壁佛龕南側的菩薩塑像是北魏時期的作品。當我們單看它的臉時,似乎格外平常,再看它的嘴,也沒有什么特別的表情。可是當我們從頭到腳來回迅速一看時,會驚奇地發現,這座塑像卻在微笑!一種恬靜而隱秘的微笑。再順著笑意往下看,那樣神秘,那樣迅速。作者用很簡練的塑造手法,留出了大量的藝術空白,讓人能覷見這一藝術奧秘,啟開那通往藝術天國的大門。
藝術的概括和刪減,是整體塑造的重要手法之一。這種藝術的“減法”往往要比塑造的“加法”難得多。因為“減法”不僅需要高度的整體概念,而且更需要膽識。法國著名雕塑家羅丹一斧頭砍去他的《巴爾扎克》塑像雙手的故事,為世人傳為佳話。在莫高窟的壁畫中,北周第296窟有這一大膽的藝術手法。第296窟窟頂四周的佛傳故事畫,畫者采用的是極簡練而又獨特的表現手法,在白色底子上僅用土紅線勾出大體,然后填鋪上所需的色塊。但仍留出大量的空白和土紅線不著色。這樣簡練的畫面,一般是很難再作刪減了的,而畫者卻把其中的許多紅土線用厚白粉作了刪減。真是簡中又“減”。筆者在該洞臨摹這些壁畫,經過反復比較才認識到這些被刪去的土紅線會阻滯人的視覺,因而也會產生繁瑣,而要刪除這些線條則形體要受到破壞。整體高于一切,古人大膽地舍“形”而取“神”,刪除了其中許多阻滯視覺暢通的線。如窟頂北壁西端微妙生孩子、丈夫喝醉敲門,并殺其子、將兒子煮了強令微妙吃其子的場面,畫者刪除了微妙房子四周墻面上的紅土線,僅剩下一個房頂。這樣非常突出了人物的動作和戲劇性高潮。這時房頂給人的感覺僅僅是一種暗示而已。這種刪去的空白正像一條疏通情感的河渠。當我們看見這些畫面時,作者要表達的情感便自然而然地流到我們心間。遠古時代雖然過去了,但是我們仍能從這些刪除的空白處看到古代的藝術大師們的整體塑造的全部才能和膽識。
源自:敦煌研究院 作者:謝成水